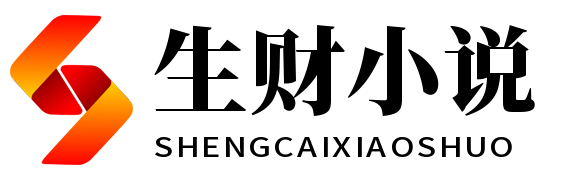小说:大商大海 小说:都市-日常 作者:倚山令 简介:新一代创业者的创业之路复杂而曲折:青年赵河马没有选择都到大城市打工寻求发展,他对古典的中国草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心发掘这门科学。他选择进深山老林拜老前辈为师,学习古典的中药和饲养双头白花蛇的技术。进山途中恰遇蛇王女儿,发生误会到冰释前嫌,到被蛇王接纳,历经艰辛,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千回百转,时而啼笑皆非,时而柔肠寸断,让人如临其景,如为其友...

《大商大海》第3章 柳暗花明会有村吗免费阅读
他在创业之路上并不顺利。一开始,他凭大浪沟坑、河、沟、汊多的特点,从外地买了一批鱼苗,养在塘里。可偏偏天不作美,一连数日大雨,沟满水流,鱼苗随着河水付之东流。听说外地养鸳鸯发了财,他借了一笔钱从外地买回来几百只,没想到长大以后全部是公鸭,天下竟有这多么骗子!
凭着年轻人的一股血气,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听说江南有养牛蛙的,就和同村好友赵良瓜又一起出来了。事有凑巧,在城里发现这卖蛇女子蛇女子,看到一条小小的白花蛇能换来一张“大团结”,他突然间又改变了主意,也是鬼迷心窍,竟悄悄跟姑娘进了山,才受了这场虚惊。
眼下,他见这姑娘问起自己的名字,不由得感到一阵难为情。
他是土生土长的乡里孩子,就连起名字也摆脱不了当地的习气。他是家里的独根苗苗,从爷爷那一辈起,到他这一辈已经是单传三代了。家乡的习惯,越是娇养的宝贝,越是起一个最下贱的名字,为的是容易养大成人。算命先生说这孩子是水命,因此,家里人就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坷垃。
谁知道这乳名一叫起来就不容易被人忘记,直到他入学的时候起了个大名,村里人还是照样叫他坷垃。
他从自己的名字中,似乎感到了一种打在身上的无形的烙印。乡下人那种挣不脱的自卑感,又使他感到惶惑和不安。
在同伴们中,他也也算是伶牙俐口,而且不乏自信和主见。但在这个神奇而又陌生的姑娘面前,他有些愕然了。
真视女性的尴尬,使他避开对方那善意嘲笑的目光,嗫嚅着说:“不怕您笑话,我小名叫坷垃。上学时,老师就用这个谐音,在报名册上写了土克拉这三个字,以后就成了我的大名。”
“嘻嘻!坷垃,真有意思。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叫这么个名字。”她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那放肆的笑声带着山里姑娘特有的野性味。“笑莫露齿,言莫高声”的古老闺训,对她是无缘的。她生长在深山老林里,长期与鸟兽为伍,她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看着五尺高的男子汉在她面前扭扭捏捏的,她感到一阵好笑,嘲弄地说:“怪不得你看到长虫这么害怕,长虫钻坷垃呀!一物降一物!”
对方的话尽管带着戏谑,他却突然感到一阵余悸。想起刚才的情景,真还使人有点后怕,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说:“你还怪会说哩,那咋不怕?我听人说,被蛇咬上一口,跑不了七步就没命了,那能是闹着玩的么?!”
“嘻嘻!”她笑得更欢了。那神态仿佛是嘲弄对方无知,又仿佛是觉得对方诚实得可爱,“我再缺德,也不会放蛇去咬人!那是一只拔过毒牙的蛇!”
“啊!原来是这样!”他长长地松了口气。猛然间,眼前这个少女的形象在他面前变得美好起来,原来这是个心地并不坏的人。“怪不得那蛇只往我脸上舔,却不咬我。”他笑了。
“别生我的气。”她替对方拾起那只破旧的黄挎包,歉意地说;“我并不是有意吓你,在这种地方,你一个男人家老在屁股后面跟着我,太阳快下山了,我不得不防。”
“不生气,不生气。”他感激地接过挎包说:“都怪我不好,惹人烦。”
她笑了。咧开的嘴像一弯月牙,以至于整个脸上都呈现出甜蜜的和谐美,一种略带野性的敦厚的美,这也许是山里人的另一种性格。误解虽然消除了,但毕竟是萍水相逢,他们是陌路人。她挎起那只精巧的细竹篮,又把篮盖扣紧,转身欲走。
“大姐……”他似乎意识到了某种结局,又急忙叫了一声。虽然刚才受了一场虚惊,总算是有了攀话的机会。如果失去了这种机会,他这趟进山不是白跑了么?
她闻声转过身来,似乎早就预料到他还有话说,静静地等待着。
他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合适,仔细地斟酌着自己的语言。可一抬头,在对方那直视的目光下又变得胆怯起来。他实在不善于和女人攀谈,特别是在这种幽静的地方一个人和年轻女子攀谈。这一瞬间,他觉得背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而这种汗和刚才头上的淋漓大汗是不同的,尽管都是由于紧张。出前一种汗时他觉得浑身发凉,血管暴胀,似乎是从身上的汗腺中拧出来的;而后一种汗是不知不觉地渗出来的细汗,他觉得脸上微微有点发热,似乎是从细胞中溢出来的。
“你这个人也真是。”她从对方那吞吞吐吐的样子里,发现这是个老实得可爱的角色,就说:“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子的,有话不会说,只会悄悄地在后面跟着。”
“我不大会说话。”他自嘲地笑了笑,歉意地说,“特别是一急,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何尝不想痛痛快快地向她说明:我是来学艺的,想向你学养双头白花蛇的手艺,回去也搞养蛇,也赚一笔钱。但是,他不能这么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外出学艺,他吃了不少闭门羹,才知道要想跟别人学点本事,实在不容易。他过去常听人说,手艺人没有一个不是自私的。也许,“同行是冤家”的这种传统观念决定了手艺人的这种自私狭隘。他听人常讲,有些绝招的手艺人,是绝不肯轻易外传的。即使在一个家庭里,有的也只传儿子,连姑娘都不传。他轻易地向别人提出学艺,人家会答应吗?
他外出学养鸳鸯那阵子,白白给人家干了好长时间的活,结果啥也没学到手。后来发发狠,从另一个地方买了百十只小鸳鸯,没想到受了骗,长大以后全是公鸭!眼下,这饲养双头白花蛇显然是一种更绝妙的手艺,她更不会轻易外传。他不得不小心从事了。
“大姐,我们那里穷得很,我想出来帮人家做个活。你能不能帮帮忙,工钱好说,给多少都行。”他思忖了一阵子,终于试探着说。
“做帮工?我们这里可不缺人哪。”她狡黠地笑了,似乎看透了对方的隐秘。“你那介绍信上不是说,想出来学养牛蛙吗?怎么又想当帮工?”
“唉,想学是想学,可谁肯教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一肚子气不觉涌上心头。一塘鱼苗随水而去,百十只小鸳鸯全变成了公鸭,几次的失败,在他心头积压了一层厚厚的阴云,不觉眼睛湿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虽然眼前这陌路女子并不是可以倾诉的知音,但他还是委婉地吐露了自己的苦衷,以期得到她的同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她也不会例外。对落难之人的冷漠和麻木,除非是铁石心肠。何况一般来说女人的心肠都是极软的,都是富于同情心的。
有道是哀兵可以制胜。果然,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表现出来的哀怨情绪,使对方受到了很大感染。她长长地叹了口,一种怜之心复苏了,深表同情地说:“想学点技术是不容易呀,非亲非故的,谁肯尽心教。就说连那贴广告的学习班吧,哪个不是为了赚钱,真本事哪里肯舍得外传。”
“谁说不是的!那些人恨不得把天下的钱都赚到他自己手里!连指头缝里都不想露出半个仔。钱越多越想赚,越多瘾越大,越怕别人学他的本。像我这可怜巴巴的人,跟谁学去!”对方的话勾起了他的起了他的伤心处,他真的动起感情来。
“就拿刚才来说吧,我原也打算跟你学点养蛇技术,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很不现实的……”他略一停顿,看了一下对方的脸色,想从对方那面孔上的细微变化中,捕捉到某种讯号。但是对方脸上没有任何讯号发出,似乎早就意识到他会这么说的。他失望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自嘲地接着说:“现在我已经心灰意冷了,什么也不想学了。既然出来了,就找个活干干,赚几个盘缠钱好回家,安安份份地过日子。”
山里女子并不乏机敏,那机敏,那闪着聪颖和智慧的眸子里,早已摄下了对方内心的秘密。她确实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叹了口气,有些为难地说:“就冲着你这点诚心,在大山里跟我这半天,我也想收留你……”
像浓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裂缝,一束祥光照顶那,他猛然感到一线希望,感到一种吉祥之神的光临。他浑身一阵颤抖,眼里闪射着喜悦之光,他凝神地听着,注视着,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唉!”她又长长地叹了口气,眉宇间笼罩着一片阴云。她似乎不愿说下面的话,可事到眼前又不得不说:“实话告诉你吧,我爹是个很严厉的人。桃花坞镇上的贾货,和我爹是多年的老相识,他想来学本事,我爹都不肯教他。当然,他们老辈人之间可能有什么难于启齿的事。不过,从我爹对贾货的态度来看,他是不肯轻易收徒弟的,我劝你还是别……”
姑娘的直言忠告,像一声惊雷,使他从五彩缤纷的幻梦中跌落下来,回到眼前严峻的现实之中。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失魂落魄地往回走去。
残阳像一盏耗尽了的豆油灯,那一点余晖早被浓浓的暮霭所吞噬。
“回来!”她朝渐渐被夜幕吞没的背影喊了一声,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滋味的喊声。也许是“境由心造”的原因,在他听起来,这声音如雷贯耳,如福音来临。他默默地停下来,在夜幕中望着那苗条的倩影和明亮的眼睛。尽管那眼睛根本不会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一样闪闪发亮,但他还是希望它晶莹发亮,像北斗星一样。也许他此刻最需要的是照亮他前程的北斗星。
“下山还有几十里路。天这么黑,你怎么回去?”她到底是个女子,想得很细。
“慢慢摸吧。”虽然对方的答话仍使他失望,但他还是感激地说:“我一个男人家怕啥,身上啥也没有,谁还会找我的麻烦。你就放心吧。”
“你没走过山路,夜里会出事的。”她仍然不放心,往前走了几步,说:“弄不好摔下去,可都是我造的孽。还是我送送你吧。”
“不,不。我怎么能让你送。”他真的受感动了,连连推辞着。尽管对方的好心使他受到了某种抚慰,但男子汉的尊严使他变得固执起来,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子送自己。“谢谢你,再见。”他失急慌忙地朝前赶去,好像迟一步会被对方抓住似的。
“回来!”她又喊了一声。这一声不算很高,但在寂静的山径上却显得很威严,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
他终于被这喊声所震慑,尽管没有回来,但还是站住了,在夜幕中静静地等待着。
她快步走到对方跟前,伸手夺过对方那破旧的挎包,说:“既然你不叫我送,那就跟我回去吧。我家快到了,在我家住一晚,明早再下山。出门在外的人也真不容易。”
“这,这……”他感到有些意想不到,一瞬间乱了方寸。
“你不是想学本事吗?”她狡黠地笑了笑,说:“见了我爹碰碰运气吧,要是你和他有缘份,兴许会传授你一点。”
“真的?”他喜出望外,两眼又冒出希望的火花,仿佛那北斗又突然间亮了起来。“我听大姐的,走!”
“别大姐大姐的叫,咱俩谁大还不一定呢!”叫得人怪难为情的。
“南京到北京,大姐是高称。”坷垃说:“叫大姐是对您的尊重并不是说您比我大。”
坷垃明白很多女孩子的心理,她们都希望自己年轻一点,很多人甚至于不轻易说出自己的年龄。别看有些女孩子骂人时张口一个姑奶奶,闭口一个老娘的,你要是真的叫她老姑奶奶或老娘的,她肯定骂死你。这就是女孩子的心理。
“是南京到北京,大哥是高称,你有没有搞错啊!”对方立即纠正的说。
“这不都一样吗?是一个理。”坷垃解释说。
“当然不一样,男女是有别的。”对方说。
“我真的不明白。”坷垃有些歉意的说。
“那我给你批讲批讲吧。”对方说:“大姐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是德高望重的人,大家都称之为大姐,这些和年龄辈分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尊称。但这些德高望重的女性一般都比较大,都有地位;还有一种就是黑社会的人也把他们的女头头称之为大姐。你说我该是哪一种呢?”
“您当然哪一种都不是。”坷垃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忌讳原因,赶忙说道。他想改口称对方妹妹,或者阿妹,但他确实不敢。哥哥妹妹这个称呼有点过分亲昵,甚至于有点暧昧;阿哥阿妹的更是电影上热恋中的男女的称呼,他不敢和对方攀亲近。如果她肯收留自己学艺的话,那更是要泾渭分明,师傅就是师傅,徒弟就是徒弟,隔着辈分呢!如果见到江南蛇王,他肯收自己当徒弟的话,那再改口叫她师妹也不迟。现在叫有点唐突,也不合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是出来求人的,自然是比别人低半截。
这也难怪坷垃的自卑心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都是这样,一辈官三辈爷,做官的称老爷,官员的父亲称老太爷,官员的儿子称少爷;久而久之的沿袭下来,大凡有权有势的人都是这样称呼,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也成了乡规民约,更成了一种文化;不知道这是一种谦恭的美德呢,还是一种扭曲的心灵。不管怎么说,千百年的无形的等级制度,随着文化因子的传承,在人们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坷垃不知说什么好了,就干脆什么也不叫,就给她来个呼哈,什么也不称呼,到她家里见到江南蛇王再见机行事。
>>>点此阅读《大商大海》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