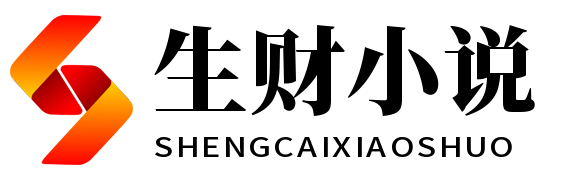军事历史《替身:开局扮演慈父?》,由网络作家“茜栎”所著,男女主角分别是阿列克谢斯大林,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详情介绍: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且看工农挥巨斧,管他元首自封官。
1941年12月19日,克里姆林宫地下指挥所的防爆门被风雪撞开,朱可夫带着满身冰碴闯入,斗篷下露出的元帅服前襟结着冰棱:“斯大林同志,德军无线电广播说,希特勒解除了布劳希奇的职务。”他的烟斗在掌心敲出火星,“那个奥地利下士,现在要亲自指挥陆军了。”
作战地图前的将领们发出低低的轻笑,莫洛托夫推了推圆框眼镜,镜片上的雾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细冰:“戈培尔的广播稿里,‘元首兼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念得磕磕巴巴,”他的声音像冻硬的铁轨,“就像让画家去指挥交响乐团。”
我盯着地图上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部署标记,那些蓝色箭头因指挥层更迭而显得犹豫:“告诉秋列涅夫,”我敲了敲西南方面军的反攻轴线,“希特勒刚兼任陆军总司令,德军参谋部正在重新校准坐标——这是切断第2集团军补给线的最佳时机。”
贝利亚的手指划过截获的德军密电,袖口的苦杏仁味混着油墨气息:“布劳希奇的免职令是在凌晨三点签署的,”他的目光扫过“元首大本营”的坐标,“德军将领们在无线电里用密码骂人,说‘下士的地图上只有啤酒馆’。”
华西列夫斯基展开叶列茨攻防图,铅笔在“奥卡河支流”处划出重笔:“我军侦察兵发现,德军补给车队依赖叶列茨老桥,”他的指尖敲在结冰的河面上,“而捷尔任斯基工厂的潜水员,三天前就在桥墩里埋了炸药。”
“让他们把炸药导火索接上啤酒瓶,”我突然说,想起在集体农庄见过的捕兽夹,“希特勒喜欢在地图上画啤酒馆,那就让他的补给线,跟着啤酒瓶一起炸上天。”朱可夫突然笑出声,震得肩章上的积雪掉落:“这个主意,该让德军后勤官们尝尝慕尼黑啤酒的味道。”
前线战报在十分钟后送达,叶列茨桥头堡的德军正在用推土机清理路障。我通过步话机听见侦察连长的汇报:“他们的工兵靴底嵌着防滑钉,”他的声音混着风雪,“和1916年东普鲁士的款式一样。”
“告诉战士们,”我摸了摸腰间的PPSh-41冲锋枪,枪托处还留着老技工伊万诺夫的焊痕,“把三角铁钉撒进桥头的积雪,让德国人的防滑钉,变成踏进地狱的门票。”步话机里传来压抑的笑声,夹杂着铁钉碰撞钢盔的脆响——那是工兵们在给冻土布置“钢铁麦田”。
莫洛托夫递来外交密电,英国战时内阁对希特勒的人事变动表示“谨慎乐观”:“丘吉尔说,这是‘独裁者的疯狂之举’。”他的镜片闪过冷光,“但我们的T-34,不需要英国的乐观主义。”
“告诉伦敦,”我指向地图上的叶列茨,那里的铁轨正在被苏军工兵撬起,“当希特勒在统帅部摔地图时,我们的工人正在把德军的铁轨,锻打成刺杀他的匕首。”通讯兵记录时,我看见他笔尖在“匕首”二字上停顿——那是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用德军钢轨锻造的刺刀代号。
下午三点,叶列茨前线传来捷报:老桥在德军车队通过时坍塌,200辆满载燃油的卡车坠入冰河。朱可夫的望远镜对准冰面,那里的德军正在抢夺漂浮的油桶,却不知水下缠着反坦克犬的磁性炸弹:“看!他们在给自己的葬礼准备燃料。”
我接过望远镜,镜头里的德军士兵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冰面上滑倒又爬起。想起在捷尔任斯基工厂看见的场景:潜水员们在零下40℃的河水里作业,用集体农庄的渔网包裹炸弹,说“这是给希特勒的圣诞礼物”。
贝利亚送来NKVD的审讯记录,一名被俘的德军参谋语无伦次:“元首每天要修改27次作战计划,”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昨天半夜,他把乌克兰方面军的部署图撕成碎片,说‘布劳希奇的防线像啤酒泡沫’。”
“告诉这个参谋,”我敲了敲审讯记录,“希特勒的啤酒泡沫,很快会被我们的喀秋莎火箭雨冲垮。”转向华西列夫斯基,“把叶列茨的铁路枕木浸上熊油,德军的火焰喷射器,烧不化冻土下的钢铁意志。”
黄昏时分,捷尔任斯基工厂的战时广播响彻指挥所:“这里是锻铁车间!我们把德军钢轨锻成了刺刀!”“纺织女工用希特勒的照片当砂纸,现在每支枪管都能咬穿坦克!”我对着送话器大喊:“告诉同志们,希特勒兼任陆军总司令的消息,比任何润滑油都更让我们的枪炮发热!”
回应我的是密集的锤打声,像极了集体农庄秋收时的脱粒场。马林科夫递来运输清单,目光落在“非常规武器”栏:“市民捐出了37吨啤酒瓶,正在熔铸成燃烧弹。”“在弹体刻上‘给元首的祝酒词’,”我笑了,“让每个燃烧瓶,都成为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纪念品。”
深夜的作战会议上,朱可夫摊开缴获的德军部署图,希特勒的亲笔批注像醉酒的蚯蚓:“他把第4装甲集群调往南方,”朱可夫的烟斗敲在高加索方向,“却不知道,秋列涅夫的骑兵军,正在用马刀收割他的后勤线。”
莫洛托夫突然站起,手中的外交急电在台灯下泛着青光:“日本驻苏大使试探性询问‘苏德局势’,他们的关东军,正在兴安岭冻掉鼻子。”“告诉日本人,”我指向地图上的“西伯利亚铁路”,“如果他们想尝尝T-34的履带,我们可以免费赠送防滑链——用希特勒的钢盔改制的。”
凌晨,我独自走进武器陈列室,斯大林1918年的马刀在玻璃柜里泛着冷光。刀柄上的防滑纹里,还嵌着当年察里津的泥土,而我后颈的伤疤,此刻正与刀鞘上的弹痕形成诡异的呼应。通讯兵突然闯入,带来叶列茨前线的速写:一名苏军士兵用德军钢盔接住桥头堡的碎木,在火上煮着麦粒粥。
“把这幅画印在《真理报》上,”我摸着画中士兵的钢盔,那里刻着“希特勒是个裱糊匠”的德语,“让德军知道,他们的元帅服纽扣,很快会成为我们熬粥的铁锅。”
正午的阳光终于穿透云层,照在叶列茨的废墟上。我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所,看着T-34坦克群碾过德军遗弃的“元首万岁”标语牌。车长们将缴获的德军元帅杖插在炮塔上,顶端的鹰徽在风雪中摇晃,像只断了翅膀的乌鸦。
“斯大林同志!”一位浑身是雪的工兵跑来,他的工装口袋里掉出半张德军作战地图,“我们在桥底发现了希特勒的画像,”他的眼睛在护目镜后发亮,“现在正用来垫着烤土豆。”
我接过地图,希特勒的画像被烤得卷曲,嘴角还沾着土豆泥:“告诉工兵们,”我指着远处正在重组的苏军纵队,“下次炸桥时,记得给画像留个座位——让独裁者的画像,永远躺在他自己挖的战壕里。”
黄昏,贝利亚带来NKVD的最新情报:“德军总参谋部内部流传着笑话,”他的声音罕见地带着笑意,“说‘元首的作战室,是用啤酒杯和油画笔布置的’。”我点头,想起在捷尔任斯基工厂看见的场景:老技工们在炮弹上刻漫画,希特勒的小胡子被画成麦田里的杂草。
“让我们的宣传员,”我指向正在播音的战地喇叭,“把这些德军笑话编成顺口溜,用喀秋莎的发射频率广播——让希特勒知道,他兼任的不是陆军总司令,而是苏联工人的锻造砧。”
深夜,朱可夫送来希特勒的最新手令,命令德军“战至最后一人”:“他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朱可夫的烟斗在地图上划出死亡弧线,“当年拿破仑也是在莫斯科近郊,亲自指挥了最后一场败仗。”
“但我们比1812年多了些东西,”我摸着地图上星罗棋布的工厂标记,“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正在给每发炮弹刻上‘希特勒去死’的德语——这些带着体温的钢铁,会让独裁者明白,工农的铁锤,比任何元帅杖都更有分量。”
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午夜,我站在地图前,看着叶列茨方向的红色箭头深深插入德军防线。那里的铁路枢纽已被收复,工人们正在用德军的铁轨铺设临时站台,枕木上的弹孔,成了最好的防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