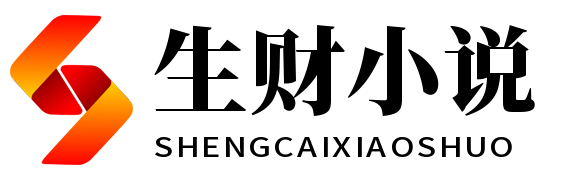主角是阿列克谢斯大林的精选军事历史《替身:开局扮演慈父?》,小说作者是“茜栎”,书中精彩内容是: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车队在冰面上排出防御阵型时,第一颗照明弹已升上夜空。青白色的光线下,30辆伪装卡车组成的菱形编队正在结冰的湖面上投下巨大阴影,每辆车车头都焊着从德军坦克上拆下来的装甲板,像一群披甲的冰原狼。我看见最前排的“熔炉号”指挥车车长探出半个身子,朝我比出三根手指——那是约定的“三级防空警报”手势。
“伊万同志,”马林科夫突然用乌克兰语低声说,这是我们出发前约定的暗语,“货箱第三层有应急信号弹,红色代表向东突围,绿色——”
“留着给破冰船发信号。”我打断他,扯下围巾遮住半张脸,露出伪造的焊工疤痕,“告诉各车,把Molotov鸡尾酒准备好,德军轰炸机最喜欢追着燃烧的卡车跑。”
引擎的轰鸣被斯图卡的尖啸撕裂时,第一枚炸弹在右前方200米处炸开。冰面剧烈震颤,瓦西里猛打方向盘,卡车在冰面上滑出五道火星,油箱盖被气浪掀飞,柴油在冰面画出蜿蜒的火线。我看见马林科夫从座位下拖出铁皮箱,里面码着裹着粗麻布的燃烧瓶,玻璃瓶颈还滴着未凝固的磷液。
“给右边的同志们!”我抓起三瓶抛向邻车,燃烧瓶在车灯下划出抛物线,砸中一架低空俯冲的Ju-87机翼。磷火瞬间吞没引擎,德军飞行员在坠机前发出的惨叫,被冰层下的回音拉得格外漫长。马林科夫突然指着左前方,那里的冰面正浮出黑色剪影——三辆德军Sd.Kfz.251装甲车破开水面,履带碾碎薄冰时溅起的水珠,在照明弹下冻成晶亮的碎钻。
“瓦西里,朝装甲车群冲!”我踹开车门,风雪灌进驾驶室,PPSh-41的枪口火光在冰面上跳动。第一梭子子弹打在装甲车观察窗上,溅起的火星映出德军士兵惊恐的脸。马林科夫探出身子,用鲁格手枪精准射击装甲车轮胎,蓝宝石袖扣在火光中闪过——那不是装饰,是他计算弹道时的反光标记。
冰面在装甲车履带下发出不祥的呻吟。我突然听见冰层开裂的闷响,比炸弹爆炸声更可怕。“所有人下车!”我拽着马林科夫跳出卡车,吉斯-5的前轮已经陷入蓝冰裂缝,柴油顺着冰缝渗下去,在幽蓝的冰湖里映出流动的光。德军装甲车显然也听见了这声音,进攻节奏出现半秒停滞,就是这半秒,让我们的燃烧瓶找到了目标。
“扔履带!”我大喊着将燃烧瓶砸向最近的装甲车,磷火顺着金属履带爬进发动机舱,驾驶员在爆炸前跳出舱门,冰面上的积雪被气浪掀飞,露出底下用红漆写的“乌拉”——不知哪位战友早已在冰面刻下的战斗口号。马林科夫突然拉住我,指向西北方的冰雾:“第二波轰炸机!十二架,分成两个编队!”
我们趴在破冰船残骸后面,碎钢板上的铁锈混着积雪刺进大衣。斯图卡的尖啸声中,我看见马林科夫从公文包掏出皱巴巴的列宁格勒地图,用铅笔在“施吕瑟尔堡”附近画了个叉——那是朱可夫约定的佯攻时间。就在第一枚炸弹落下的瞬间,远处的冰面突然炸开十几道水柱,苏军的岸防炮开始怒吼,炮弹在德军轰炸机编队中开出红色花火。
“是‘北极星’号破冰船!”瓦西里从残骸后探出头,脸上抹着煤灰和血迹,“他们用船头的破冰斧砍断了德军的声呐线!”我看见那艘熟悉的64号破冰船正全速驶来,船头犁开的冰道里,浮出数十具德军潜艇残骸,都是女领航员曾提到的“湖底墓碑”。
德军装甲车的火力突然转向破冰船,穿甲弹在船身打出碗口大的洞。我抓住马林科夫的手腕,指向左侧正在集结的卡车:“让三辆装满工兵铲的车去堵冰裂,其余车辆组成火墙——用燃烧的卡车挡住德军视线!”马林科夫点头时,我注意到他的公文包拉链已经崩开,里面露出半张干部调动名单,第17行写着“伊万·西多罗夫,列宁格勒临时党委”,墨迹还未干透。
燃烧的卡车一辆接一辆横在冰面上,火舌舔舐着德军装甲车的观瞄镜。我带着瓦西里和两名焊工冲向最近的装甲车,他们腰间别着焊枪,此刻成了最趁手的武器。焊枪喷出的高温火焰融化了装甲车的履带,金属冷却时的爆裂声,与我们的喊杀声混在一起。当焊工伊万诺夫用焊枪在装甲车侧面刻下“斯大林”时,里面的德军士兵终于举着白手帕投降,手帕上还沾着没吃完的黑面包——和我们口袋里的一模一样。
凌晨五点,德军的第三波攻击开始前,冰面突然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马林科夫把耳朵贴在冰面上,突然笑了:“是列宁格勒的守军在敲莫尔斯电码,他们说‘我们看见红星了’。”他掏出怀表,指针正指向与朱可夫约定的时间,“西方面军的佯攻开始了,德军在勒热夫的防线出现十个缺口。”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黎明前。一架德军Me-109战斗机突破苏军防空网,机枪扫射在冰面上打出一串火花。我看见马林科夫扑向一辆正在漏油的卡车,用身体挡住油箱阀门,子弹在他大衣上打出三个洞,却没伤到要害——后来才知道,他在公文包里装了三块德军弹壳打成的钢板。
“伊万同志,看左边!”瓦西里的喊声里带着哭腔,一辆失控的燃烧卡车正朝破冰船方向滑去,车上装着给列宁格勒的医疗物资。我抓起最后两罐汽油,冲向卡车的必经之路,在冰面上泼出一条火线。当战斗机再次俯冲时,我点燃了汽油,蓝色火焰腾空而起,形成一道火墙,迫使德军飞行员拉升高度,错过了致命的投弹角度。
晨光初绽时,德军的攻势终于退去。马林科夫坐在碎冰上,用雪擦拭鲁格手枪,蓝宝石袖扣在朝阳下闪着微光:“贝利亚的密电,说我们的车队在德军侦察机照片里,像一群踩着火焰奔跑的北极熊。”他忽然掀开我的大衣,检查是否有伤口,目光落在我胸前的焊工证件上,“伊万·彼得罗夫同志,你的证件照片该换了——现在这张脸,更像列宁格勒的破冰船船长。”
我们站在燃烧的卡车残骸旁,看着破冰船的船员们跳下车,用缆绳固定住即将沉没的吉斯-5。女领航员从船头跑来,围巾上的冰棱已经融化,露出底下绣着的红星:“斯大林同志,”她突然用本名呼唤,又立刻改口,“伊万同志,列宁格勒的孩子们在防空洞画了路标,只要跟着冰面上的红星箭头走,就能避开所有德军雷区。”
我注意到她手中握着半块黑面包,上面用糖霜画着小小的坦克——和捷尔任斯基工厂女工们的手艺一样。远处,马林科夫正在协调伤员转移,他的公文包不知何时换成了德军的弹药箱,里面装着从装甲车缴获的德军作战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所有潜艇埋伏点。
下午三点,车队重新整队时,冰面上多出三十具德军尸体,他们的钢盔被整齐地摆成箭头,指向列宁格勒方向。马林科夫递给我一块从德军指挥官身上搜出的怀表,表盘停在1941年12月31日——正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开会的那天。“他们的时间,”他敲了敲停转的指针,“永远留在了苏维埃的冬天。”
夜幕降临前,我们遭遇最后一次袭击。三辆德军轻型坦克从冰面下的隧道钻出,履带碾碎冰层时带起的水花,在探照灯下如同银色的幕布。我让车队熄火,命令所有士兵用焊枪在冰面制造反光,模拟大规模部队集结的假象。德军坦克果然犹豫了,就在他们调整炮口的瞬间,破冰船的船头撞向最近的坦克,装甲板与冰面摩擦的火星,照亮了坦克侧面的编号——正是去年夏天在明斯克缴获的苏军T-26。
“用他们的炮打他们!”我大喊着冲向坦克,马林科夫已经撬开舱盖,用鲁格手枪逼出里面的德军乘员。当我们调转炮口时,发现瞄准镜里的十字线早已被焊枪烧歪——不知哪位列宁格勒的工人,早已在坦克出厂前埋下了这样的“礼物”。
1月4日凌晨,当车队终于看见列宁格勒城头的探照灯时,拉多加湖的冰面开始传来轻微的震动。马林科夫指着东方,那里的天空泛着铁青色,像极了捷尔任斯基工厂的锻铁炉:“朱可夫的电报,西方面军提前三小时突破德军防线,现在正在向勒热夫市中心推进。”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铁盒,里面是莫斯科带来的盐粒,“等进了城,把这个撒在德军的尸体上,就像当年在察里津烧粮仓时那样。”
卡车驶过最后一道冰裂时,我看见冰面下漂着德军的劝降传单,彩色油墨在幽蓝的冰水中晕开,像极了苏维埃的红旗。女领航员突然唱起《列宁格勒交响曲》的片段,破碎的旋律被风雪撕扯,却让所有司机跟着哼起了调子。马林科夫的手指在膝盖上敲着节拍,蓝宝石袖扣终于不再掩饰,在车灯下划出明亮的弧线——那是胜利的信号,是千万人用血肉在冰原上写下的乐谱。
接近城郊时,前方突然出现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德军,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他们举着油灯、火把,甚至是用德军头盔改制的灯笼。一位老妇人捧着陶罐挤到车前,里面是温热的甜菜汤,汤面上漂着几片用德军传单折的纸船:“伊万同志,”她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着泪,“这是我们藏了三个月的甜菜根,知道你们要来,特意煮了汤。”
我接过陶罐,热气熏得人眼眶发潮。马林科夫突然蹲下身,帮老妇人系紧围巾,他的大衣下摆露出半截绣着红星的布料——那是从德军军旗上剪下的,此刻成了最温暖的补丁。远处,传来防空警报解除的长鸣,不是因为安全,而是因为列宁格勒的守军,已经用血肉之躯,为我们的车队筑起了一道永不崩塌的冰墙。
当第一辆卡车碾过德军的封锁线标志时,我摸了摸胸前的焊工证件,上面的照片不知何时被风雪磨得模糊,却让“伊万·彼得罗夫”的面容,与冰面上所有坚韧的灵魂重叠。马林科夫望着逐渐清晰的城市轮廓,低声说:“1917年我在冬宫看见过列宁,他说‘城市是人民的堡垒’。现在,列宁格勒的每块砖都是堡垒的基石,而我们,只是把红旗插向基石的人。”
冰湖的夜风依然凛冽,但卡车驾驶室里,老妇人的甜菜汤还冒着热气。我知道,这场在拉多加湖面上的战斗,不是终点,而是另一场更严酷战役的开始。当车轮碾过德军留下的弹坑,当焊枪的火花再次在冰面亮起,我终于明白,所谓领袖的成熟,不是学会伪装,而是在枪林弹雨中,依然能听见人民的心跳,依然能让自己的脉搏,与千万个冻僵的手掌,共同敲响胜利的战鼓。
凌晨五点,车队抵达列宁格勒近郊的“生命之路”终点。迎接我们的,是一群戴着水兵帽的少年,他们举着用德军铁丝网编成的花环,上面缀着拉多加湖的冰花。最年长的男孩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袖口露出的伤疤,与我在会场见过的伤兵、工厂的焊工、破冰船的船员,都那么相似——那是苏维埃人民在冰原上锻造的勋章,是比任何伪装都更真实的身份证明。
卡车熄火时,马林科夫忽然指着远处的城市灯火,那里的每扇窗户都闪着微光,像落在冰原上的星星。“看,”他说,“列宁格勒的灯,从来没灭过。”我点点头,握紧了手中的PPSh-41,枪托上的刻痕还带着体温。是的,这座城市的灯不会灭,因为每个在冰面上战斗的人,都是一盏灯,而我们,正用血肉之躯,将这些灯光连成一片,照亮整个苏维埃的寒冬,直到迎来属于人民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