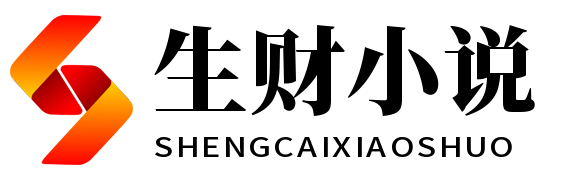军事历史《替身:开局扮演慈父?》,是小编非常喜欢的一篇军事历史,代表人物分别是阿列克谢斯大林,作者“茜栎”精心编著的一部言情作品,作品无广告版简介: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斯大林同志!”远处传来呼喊,几个工人举着修复的T-34炮塔零件跑来,上面用焊枪刻着“乌拉”。我摸着凹凸不平的字迹,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字母歪了,像极了妹妹在冻土上写的字。“是我们厂长刻的,”年轻的焊工说,“他昨天在抢修时被弹片划伤,却笑着说‘正好给坦克纹个身’。”
下午,朱可夫带来沾满雪粒的战报,反坦克犬部队共摧毁德军57辆坦克,训导员生还率不足20%。“他们本可以活下来的,”他盯着名单上的年轻名字,“这些猎人本该在西伯利亚追驯鹿。”“但他们选择了追坦克。”我打断他,目光落在窗外正在融化的冰棱,“就像工厂的女工选择了扳手,农民选择了步枪——这就是苏联。”
深夜,地堡的座钟指向零点,我独自对着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出神。德军的蓝色浪潮在红色防线前退潮,留下无数钢铁残骸,而苏军的反击箭头正刺入敌人的侧腹。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火光在远方闪烁,那不是爆炸,而是加班的灯火——工人们在铸造新的炮弹,为明天的进攻准备牙齿。
朱可夫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他送来最新的航拍照片:莫斯科近郊的田野里,无数黑点在移动——那是市民们在修筑反坦克壕,用铁锹、镐头,甚至徒手挖开冻土。“他们在给坦克准备坟墓。”朱可夫说,声音里带着少见的温柔,“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在搬运鹅卵石。”
我摸着地图上的“伊尔库茨克”,那里的焦土带已被白雪覆盖,像盖上了一层干净的棉被。妹妹或许正在某个疏散营里,听着胜利的消息,却不知道哥哥早已变成报纸上的画像。后颈的伤疤突然发痒,我知道,那不是冻伤,而是谎言在严寒中结出的痂——等到春天来临,这些痂会脱落,露出下面真正的苏联,由农民的血、工人的汗、士兵的骨共同铸就的钢铁之国。
德军的最后一批轰炸机在远方哀鸣,却再没勇气低飞。我戴上大檐帽,镜中人的目光与墙上斯大林的画像重合,后颈的伤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像朵永不凋谢的罂粟。朱可夫推门进来,身后跟着浑身是雪的通讯兵,他敬礼时,肩章上的红星抖落冰碴:“西伯利亚第20集团军抵达前线,士兵们说,他们的枪管在-40℃还能喷火。”
“让他们把火喷向柏林。”我接过战报,指尖划过“PPSh-41冲锋枪正常使用”的记录,突然想起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她们在机床前呵气暖手的模样。现在,这些带着体温的武器正在前线咆哮,就像那些反坦克犬、那些维修坦克的工人、那些在焦土中播种的农民——他们都是斯大林,都是苏联,都是冻土上永不低头的钢铁之魂。
铁蹄碾碎三冬雪,匠手拧成九曲肠。
且看棋盘争劫处,工兵自有妙文章。
1941年11月17日凌晨,克里姆林宫地下指挥所的橡木长桌被作战地图铺满,朱可夫的手指如铁钳般扣在加里宁防线的褶皱处,指甲几乎戳穿纸面:“古德里安把第4装甲集群压在莫斯科西北,我们需要在北线撕开缺口。”他抬头时,镜片上的蒸汽模糊了视线,“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在克林消耗太大,必须让德军首尾难顾。”
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推过等高线图,铅笔在“加里宁—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一线画出密集的三角符号:“工兵部队发现,德军摩托化纵队依赖M10公路,那里的冻土含水量高,车轮打滑率比其他路段高37%。”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针叶林带,“如果在路基下埋设三角铁钉——”
“用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废钢材。”我接过话头,想起三天前在工厂看见的废铁堆,“让工人们把边角料锻造成三棱形,每枚钉尖淬毒,零下30℃仍能穿透德军轮胎。”朱可夫的烟斗突然点燃,火光映出他紧绷的下颌线:“需要多少工兵?”“3000人,今晚出发。”华西列夫斯基翻开笔记本,“他们携带雪橇犬运输铁钉,利用夜雾掩护。”
贝利亚的身影突然从阴影里浮现,袖口的苦杏仁味盖过了烟草气:“斯大林同志,”他递上加密电文,“南方方面军报告,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在罗斯托夫遭遇游击队袭扰,后勤线中断48小时。”电文末尾用红笔圈着“德军首次被迫后撤”,这行字在台灯下像道新鲜的伤口。
朱可夫的拳头砸在桌面上:“机会!”他的烟斗指向高加索方向,“如果迫使希特勒抽调第4航空队南下,莫斯科上空的德军轰炸机将减少60%。”华西列夫斯基点头,铅笔在地图上画出弧线:“第56集团军已在罗斯托夫近郊集结,只等——”“等一个支点。”我打断他,目光落在贝利亚胸前的勋章,“贝利亚同志,让NKVD的爆破队伪装成德军工兵,炸毁顿河上的桥梁。”
贝利亚的瞳孔收缩,随即露出惯有的冷笑:“需要30名会说德语的特工,他们的家人……”“都在疏散营。”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们,桥梁崩塌时,他们的孩子会在报纸上看见‘苏联英雄’的勋章。”
凌晨三点,工兵部队的出发报告送达。我站在通讯中心,听着步话机里传来的低语:“铁钉铺设完毕,坐标M10公路37至42公里段。”那是捷尔任斯基工厂的钳工伊万诺夫的声音,三天前他还在给T-34坦克焊炮塔,此刻正在零下30℃的旷野里埋设钢铁陷阱。朱可夫突然指着实时战报:“德军第7摩托化师进入伏击区!”
观测镜里,雪亮的车灯刺破雾霭,第一辆装甲车突然失控,轮胎爆破声在寂静的雪原格外刺耳。后续车辆慌忙转向,却碾中更多三角铁钉,金属与冻土的摩擦声像极了集体农庄的脱粒机。华西列夫斯基握紧拳头:“阻滞时间至少12小时!”朱可夫的烟斗终于露出火星:“罗科索夫斯基的骑兵军可以冲锋了。”
11月19日正午,罗斯托夫前线的捷报随雪花一同飘进地堡。南方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的加急电报写着:“克莱斯特已下令后撤,第1装甲集团军丢弃200辆装甲车。”朱可夫用红笔在地图上圈住撤退路线,突然抬头:“希特勒的反应呢?”贝利亚递上截获的德军密电,译电员的字迹带着兴奋:“第4航空队正从莫斯科方向南调,明晨抵达顿河畔。”
“调第20集团军的喀秋莎火箭炮到莫斯科近郊。”我敲了敲地图上的防空阵地,“既然德国人喜欢在夜间轰炸,就让他们尝尝钢铁暴雨。”华西列夫斯基犹豫道:“但火箭炮需要校准——”“不需要校准,”我想起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把发射坐标设为德军机场跑道,剩下的交给抛物线。”
黄昏时分,罗科索夫斯基的电话从克林前线打来,他的声音混着炮火轰鸣:“反坦克犬部队在针叶林重创德军第3装甲师,”顿了顿,声音低下来,“但训导员们……”“把他们的犬舍改造成纪念碑,”我打断他,“每个犬舍刻上训导员和军犬的名字,就建在莫斯科儿童公园。”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敬礼声:“明白了,斯大林同志。”
朱可夫突然指着地图上的加里宁防线:“德军第9集团军开始抽调兵力南下,我们的牵制成功了。”他转向华西列夫斯基,“第29、31集团军可以发起总攻,目标:切断德军北方补给线。”中将的铅笔在地图上划出凌厉的箭头,像道即将愈合的伤口。
深夜,贝利亚带着满身霜气闯入,手中的文件夹滴着冰水:“NKVD在罗斯托夫俘虏了德军工兵营长,”他抽出照片,俘虏的钢盔上刻着“为了慕尼黑”,“他供认,克莱斯特的撤退是因为燃油管道被冻裂——”“不,是因为你们炸断了顿河桥梁。”我接过审讯记录,“告诉秋列涅夫,乘胜追击,别给德国人重整旗鼓的机会。”
华西列夫斯基突然站起,手中的等高线图被灯光照亮:“如果南方集团军群崩溃,希特勒将被迫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至少两个装甲师,”他的手指划过乌克兰草原,“那里的冻土比莫斯科更仁慈。”朱可夫冷笑:“仁慈?德军在基辅的万人坑可没体现仁慈。”
11月20日凌晨,捷尔任斯基工厂的代表突然造访,领头的老技工捧着生锈的三角铁钉:“这是战场上捡回来的,”他的手掌还留着焊接时的疤痕,“工人们说,每枚铁钉都是战士。”我接过铁钉,三棱形的尖端闪着冷光,想起三天前在工厂看见的场景:女工们用婴儿摇篮的废铁锻造兵器,摇篮曲混着锻铁声。
“告诉工人们,”我将铁钉按在地图上的M10公路,“这些铁钉会成为德军的墓志铭。”老技工突然流泪,他的儿子正在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里,“斯大林同志,我儿子说,看见您在红场阅兵,他就不怕死了。”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掌心触到工装下凸起的肋骨——那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印记。
正午的阳光终于穿透云层,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上。朱可夫摊开最新的兵力部署图,蓝色德军箭头在莫斯科周边出现断裂,红色苏军反击线如毛细血管般渗入敌人腹地:“加里宁方面军已推进20公里,罗斯托夫的德军正在焚烧辎重。”他的烟斗指向南方,“克莱斯特的撤退,是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处裂痕。”
贝利亚的密报再次送达,这次是希特勒的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后撤,违令者枪毙。”我将电报甩给朱可夫:“告诉古德里安,”我指了指窗外的雪原,“这里的冻土不相信命令,只相信钢铁和鲜血。”
深夜,华西列夫斯基带着改良后的三角铁钉模型闯入,尖端镀着一层锡:“工厂的化学家说,这样能防止低温脆化,”他的眼睛熬得通红,“现在每枚铁钉的寿命延长4小时。”朱可夫接过模型,在掌心掂量:“足够让德军的摩托化部队变成步兵。”
通讯兵突然冲进来,带来罗斯托夫的航拍照片:德军坦克整齐地停在旷野,炮塔指向天空——那是集体投降的信号。贝利亚的嘴角终于露出笑意:“克莱斯特创造了德军历史,”他说,“第一次在东线后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