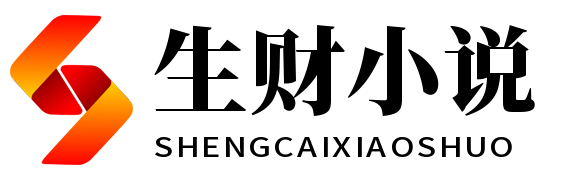小说《替身:开局扮演慈父?》是作者“茜栎”的精选作品之一,剧情围绕主人公阿列克谢斯大林的经历展开,完结内容主要讲述的是: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初雪压檐铁靴急,寒车碾梦向京畿。
地灯如狱照苍颜,镜里相逢鬓已稀。
1941年11月7日,德军即将进入莫斯科城郊。
莫斯科时间凌晨三点四十六分,克里姆林宫地下三层的医务室里。斯大林的右手突然抽搐,烟斗从指缝滑落,在瓷砖地面撞出暗哑的响,火星溅在雪白的床单上,像德军轰炸机投下的第一枚燃烧弹。
“同志,该用止痛药了。”护士叶莲娜捧着搪瓷盘的手在发抖,盘里的吗啡注射液折射着煤油灯的光,在领袖凹陷的眼窝里晃成细碎的银片。
老人却挥开她的手,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滚动,像块即将沉入冰湖的鹅卵石:“去找贝利亚,把阅兵演讲稿再改一遍……”话未说完,剧烈的咳嗽撕扯着单薄的胸膛,肋骨在衬衫下绷成嶙峋的栅栏,惊飞了窗台上栖息的麻雀——它们误把地堡通风口当成了春天的树洞。
此时的伊尔库茨克,初雪正以每分钟三毫米的速度覆盖集体农庄。阿列克谢·西多罗夫的手指刚触到草窝里第七枚鸡蛋,蛋壳表面的温度还带着母鸡伏卧时的余温,指腹碾过粗糙的壳面,能感觉到细密的气孔在传递着生命的震颤。
木门外的积雪突然发出“咯吱”轻响,不是雪花坠地的酥软,而是皮靴碾过冻硬雪壳的脆裂。
他的后颈猛地绷紧,像被狼盯上的驯鹿。去年冬天,粮仓书记在办公室吞服氰化物前,就是这种令人寒毛倒竖的寂静。掌心的鸡蛋传来细碎的“咔嗒”声,不是蛋壳破裂,而是门轴转动时,金属与木门摩擦发出的锈蚀声响——这扇用西伯利亚松木打的门,已经十七年没上过润滑油了。
冷风灌进门缝的瞬间,苦杏仁味像把钝刀剜进鼻腔。阿列克谢转身时,看见两个戴大盖帽的男人堵在门口,高个子的马裤膝盖处沾着暗红泥点,那是莫斯科红场特有的砖灰,混着融雪后结成的冰碴,在晨光中像极了三年前集体农庄大火时,烧糊的麦穗黏在铁锹上的焦痕。
矮个子的皮靴正碾过灶台边的黑面包,铁掌碾碎面包的脆响中,麦香与皮革保养油的气味诡异地融合,让人想起村东头铁匠铺里,铁锤砸在烧红马掌时,迸溅的火星灼烤毛发的焦臭。
“阿列克谢·西多罗夫?”高个子开口时,帽檐阴影里的眼睛眯成两道冷缝,喉结在浆洗笔挺的制服领章下滚动,领章边缘的金线绣着的不是常见的麦穗,而是几乎看不见的双剑交叉图案——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处的标志。
阿列克谢攥紧鸡蛋的手背上,昨天磨镰刀时崩裂的血痂突然迸开,咸腥的血珠渗进蛋壳裂缝,混着生鸡蛋的涩味在舌尖蔓延,他忍不住用舌尖抵了抵上颚,那里还留着昨夜啃黑面包时硌出的血泡。
矮个子突然跨前半步,手掌像铁钳般掐住阿列克谢的后颈,拇指碾过光滑的皮肤,指腹的老茧刮得皮肤生疼。这个动作如此熟悉,让阿列克谢想起十二岁那年,集体农庄的兽医检查新生牛犊时,也是这样捏住小牛的后颈皮。
“和1935年档案照片一样,”矮个子的声音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皮肤没晒黑,后颈弹片伤的位置……”他的指尖突然用力,在光滑的皮肤上按出红印,“这里本该有三厘米的月牙形疤痕,现在却像初生婴儿的屁股般光滑。”
老母鸡在鸡窝里发出惊恐的啼叫,扑棱翅膀带起的木屑纷纷扬扬,有片碎木刺扎进阿列克谢的掌心,他却感觉不到疼痛。高个子已经掏出了手枪,枪管垂在身侧,枪口却有意无意地指向灶台。
——那里炖着的土豆糊已经烧干,锅底传来的焦香混着雪的冷冽,在空气中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带走。”高个子的命令简短如枪声。阿列克谢被拽出门时,瞥见木屋烟囱里冒出的淡蓝炊烟,那是妹妹娜塔莎在烧早上的洗脸水。
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撒了把碎玻璃,他看见妹妹站在屋檐下,手里攥着昨天剩下的黑面包碎渣,十二岁的小脸冻得通红,辫梢结着冰碴,正望着这边拼命挥手,袖口露出的半截绷带,是用去年秋天的向日葵秸秆灰染成的淡黄色。
卡车停在村口的桦树林边,车身漆着的暗红五角星被泥灰盖成铁灰色,车门编号“ГБ-41”的油漆剥落,露出下面的黑色底漆,像道狰狞的伤疤。后车厢的铁门一开,潮气混着汽油味和铁锈味扑面而来,阿列克谢踉跄着摔进去时,膝盖磕在生锈的铁板上,手心里的鸡蛋“啪”地碎裂,蛋液顺着指缝流到手肘,黏糊糊的液体里还混着碎蛋壳,像极了去年春天,他在麦田里摔碎的那只知更鸟蛋。
车门“咣当”一声锁死,驾驶室传来高个子的低语:“别弄死,老头子要亲自验看。毕竟这可是他越过贝利亚,直接下来给我们两个的命令,比列宁墓的花岗岩还硬。”
矮个子的笑声像生锈的弹簧在跳动:“放心,瞧瞧这细皮嫩肉的,比咱们在列宁格勒抓的那些德国间谍可金贵多了。你说老头子从哪儿找到这么个活脱脱的影子?”
卡车在结冰的土路上颠簸了三天,车窗上的霜花结了又化,化了又结。阿列克谢蜷缩在车厢角落,透过铁栏缝隙,看见沿途的村庄大多空无一人,偶尔闪过几个穿军大衣的士兵,背着步枪在雪地中行进,他们的皮靴踩在积雪上,留下的脚印很快被新雪覆盖,像从来没存在过。
高个子偶尔爬进车厢,往他嘴里塞硬邦邦的黑面包,面包上还带着体温:“省着点吃,现在莫斯科的面包配额降到每天200克了,连克里姆林宫的厨子都在煮松针汤。上个月我亲眼看见,贝利亚同志的秘书在办公室偷藏了半块黄油,被发现后直接送去了惩戒连。”
第三天傍晚,卡车在一处检查站被拦下。探照灯的强光扫过车厢时,阿列克谢赶紧闭上眼睛,却还是看见哨兵步枪上的刺刀在雪地里投下的影子,像极了村口老教堂的尖顶。驾驶室传来争吵声:“莫斯科戒严了!没有最高统帅部的特别通行证,别说卡车,连只带翅膀的麻雀都别想飞进去!”高个子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平时没有的狠戾:“我们带的是……”接着是证件翻动的“哗哗”声,金属扣环的轻响,然后是哨兵敬礼的“咔嗒”声:“抱歉,同志,放行!”
卡车重新启动时,矮个子隔着铁栏递来半块黑面包,这次没有体温,只有冰冷的硬壳:“听见了吗?德军已经突破维亚济马防线,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正在向莫斯科西郊推进,离克里姆林宫只剩200公里。昨天的《真理报》头版还说‘莫斯科永远是苏维埃的’,可你瞧瞧窗外,连列宁格勒的老鼠都在往东边跑。”
抵达莫斯科时,天刚蒙蒙亮,整座城市笼罩在灰蓝色的薄雾中,像被放进了巨大的冰窖。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线照在红场附近的建筑上,列宁墓的尖顶像一柄插在地上的银刀,冷冷地闪着光,墓前的长明灯在风中摇曳,仿佛随时会被刺骨的寒风熄灭。卡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高个子扔给阿列克谢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半张脸:“跟着走,别抬头,路边的哨兵会开枪打任何东张西望的人。上个月有个老太太多看了两眼克里姆林宫,现在正在卢比扬卡监狱里数墙缝呢。”
穿过三条逼仄的巷子,他们钻进一扇漆着铁十字的木门,门轴转动时发出“吱呀”的声响,仿佛每道木纹里都藏着无数秘密。楼梯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墙壁上的墙皮剥落,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块,像凝固的血迹,每踩一步,木板就会发出“咯吱”声,像是有人在耳边轻声警告:“别回头,别回头。”
下到二十级台阶时,远处传来沉闷的炮声,地堡的墙壁微微震动,像是大地在呻吟,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有粒沙子掉进阿列克谢的眼睛,他却不敢伸手去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