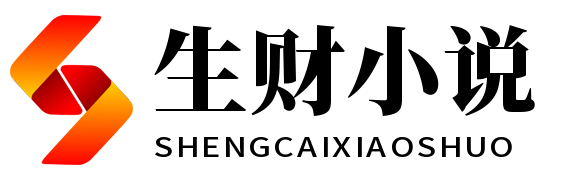由小编给各位带来小说《替身:开局扮演慈父?》,不少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下面就给各位介绍一下。简介: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糖块在齿间碎裂的瞬间,我想起1919年在察里津,同样的甜混着硝烟味,同样的信念在重围中发酵。马林科夫递来的干部名单上,列宁格勒党委成员的名字后标着“1941年12月牺牲”的红叉,最新补充的名字是“伊万·西多罗夫”——和我曾经的姓氏只差一个字母。
“就这么定了。”我敲了敲桌面,让糖块的碎屑聚成列宁格勒的轮廓,“明天凌晨三点,我以‘钢铁人民委员’的身份随运输车队出发。莫洛托夫同志,你负责向英美使节透露‘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近郊视察’;贝利亚同志,确保冰面下的潜艇在我们通过时沉默;朱可夫同志,把西方面军的佯攻时间定在我们过桥的那一刻——让德军以为我们的元帅杖,真的能劈开冰湖。”
朱可夫突然站起,军大衣带起的风扑灭了桌上两根蜡烛:“我陪您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前天来电,说守军把每栋楼的外墙都凿成了射击孔,连幼儿园的积木都堆成了路障——他们需要看见,当年在察里津烧粮仓的人,现在要在列宁格勒的冰墙上点火。”
“你留在莫斯科更有用。”我按住他肩膀,感受着勋章带硌手的硬度,“当我们的卡车碾过德军封锁线时,需要你的地图上多出十个红色箭头,让希特勒的参谋们在柏林的地堡里算错小数点。”
谢尔巴科夫突然举起份油印传单,那是德军空投的劝降书,背面不知被谁用红笔写满了列宁格勒市民的决心:“他们说,‘我们的牙齿是钢铁,喉咙是火山,就算咽下最后一口雪,也要喷向法西斯的脸’。”他的声音像在朗诵《共青团员之歌》的歌词,“这样的人民,值得他们的领袖穿过封锁线。”
会议结束时,东方泛起铁锈色的光。贝利亚留下的应急预案摊开在桌上,冰面运输线的每个拐点都标着暗语——“麦穗”代表粮食车,“扳手”代表武器箱,而“熔炉”,是我乘坐的指挥车编号。莫洛托夫临出门前突然转身,镜片在晨光中反着冷光:“1939年您视察列宁格勒时,曾在基洛夫工厂的齿轮上刻下‘工人阶级的铁拳’。现在,那个齿轮正在某辆KV坦克的履带上,碾碎德军的冬季伪装。”
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手指无意识地抚过桌沿——那里刻着不知哪位代表留下的“乌拉”,笔画边缘还带着新鲜的木屑,像是用步枪刺刀刚刻上去的。当卫兵收走冷透的茶杯,朱可夫突然凑近,烟斗的青烟拂过我耳畔:“1918年您去察里津前,列宁说‘要把那里变成燃烧的熔炉’。现在的列宁格勒,已经是座冻不坏的高炉,就等您去敲第一锤。”
上午十点,我站在捷尔任斯基工厂的装甲车间,看着女工们往“熔炉号”坦克的炮塔上镶嵌红星。最年长的锻工师傅递来副焊枪手套,掌心位置绣着极小的列宁格勒地图,冰面运输线的车辙用金线绣成麦穗形状:“同志们连夜赶制的,”他的声音盖不过锻锤轰鸣,“手套内层缝着二十片德军弹壳,能挡三发步枪子弹。”
手套戴上时,指尖触到金属的冷意。车间广播突然响起《国际歌》,不是唱片,是列宁格勒电台的直播——背景声里混着防空警报和铁锹砸冰的巨响,播音员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音:“现在播送列宁格勒少先队员的决心书:‘我们每天省下的面包渣,够造一颗子弹;我们收集的冰雪,够冷却一门大炮……’”
女工们停下手中的活,焊枪的火花在她们睫毛上跳动,像忍住不落的泪珠。我摘下手套,按在刚锻造好的装甲板上,体温在钢铁表面留下模糊的掌印——就像三天前在会场,农民代表用带冰碴的麦穗在我掌心留下的印记。
“把这个带上。”锻工师傅塞给我个铁皮盒,里面装着用坦克履带碎片打的戒指,环身刻着“生命之路”的缩写,“轮机长说,等您站在列宁格勒城头,把这戒指套在德军的炮管上,咱们的破冰船就能顺着炮口开进波罗的海。”
下午,米高扬带着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专员来了,帆布包里装着伪造的运输单据和冻成砖块的浓缩口粮。“这是最新改良的‘列宁格勒面包’,”他敲了敲铁盒,里面传来冰块碰撞的响,“用木屑、甜菜渣和德军空投的‘劝降巧克力’熔制,每块能维持三天热量。”
我尝了尝,木屑的粗糙混着巧克力的甜腻,在舌尖结成奇异的硬块。米高扬突然压低声音:“贝利亚同志私下调了一个伞兵营埋伏在湖西岸,他们的降落伞是用德军军旗改的,上面绣着‘为了斯大林’——”
“告诉他,把精力放在破译德军密码上。”我打断他,望着窗外正在装载物资的车队,卡车引擎声与工厂汽笛交织成战歌,“列宁格勒不需要埋伏,需要的是直面暴风雪的旗帜。”
黄昏时分,莫洛托夫送来英国大使的密信,信封上的火漆印还带着伦敦的暖意:“丘吉尔阁下想知道,您是否真的相信‘靠意志就能打赢冬季战争’。”他的手指划过信末的“祝好”二字,像是在冷笑,“我回信说,苏维埃的意志,是用每块面包、每发炮弹、每个冻僵的手掌锻造的。”
“下次让大使去列宁格勒看看。”我把信页凑近油灯,火光照亮信纸上的英文威胁,“让他尝尝125克黑面包的味道,听听冰面下潜艇的噪音,再告诉丘吉尔,当他在唐宁街烤火时,我们的人民正在把‘意志’二字,刻进德军的骨髓。”
午夜,贝利亚亲自检查了我的伪装——褪了色的棉大衣,磨破的皮靴,内袋里装着伪造的“钢铁工人证件”,姓名栏写着“伊万·彼得罗夫”,职业是“破冰船轮机长”。他的手指划过证件上的钢印,突然说:“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的地下通道系统扩建了30%,图纸在您大衣内袋的夹层里。”
我点头致谢,注意到他这次没戴氰化物香囊,袖口只有淡淡的油墨味——那是连夜赶制假证件时沾上的。当这位令人畏惧的内务部长转身时,我看见他大衣下摆绣着极小的红星,针脚歪扭,像是某个女工在炮塔上刻字时的手艺。
凌晨两点,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了十二下——不是报时,是为出发的车队送行。朱可夫站在石阶下,身旁停着辆覆盖着积雪的吉斯-5卡车,车斗里堆满伪装成货物的电台和医疗箱。他往我手里塞了把PPSh-41冲锋枪,枪托上刻着“察里津1918”的字样:“备用弹匣在驾驶室脚垫下,里面的子弹,每发都淬过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火。”
我抚摸着枪托上的刻痕,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不是士兵,是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她们举着焊枪组成火炬,在雪地里照亮车队前行的路。最前面的少女学徒挥舞着用德军军旗改的旗帜,旗面在夜风中猎猎作响,露出底下用银线绣的“列宁格勒必胜”。
卡车发动时,收音机里传来列宁格勒电台的声音,这次是个男孩的朗诵:“我们的老师说,等胜利了,要把德军的头盔收集起来,在涅瓦河畔种满向日葵。现在,我在防空洞的墙上画下向日葵,每片叶子都是T-34的履带印……”
车轮碾过雪地,压碎了德军空投的劝降传单。我望着后视镜里逐渐缩小的克里姆林宫红星,想起今早莫洛托夫说的话:“列宁格勒是苏维埃的眼睛,失去它,我们将看不见胜利的方向。”而现在,我要成为这双眼睛的睫毛,替千万人挡住风雪,让目光永远投向东方的黎明。
卡车驶上冰面时,拉多加湖的夜风像刀子般割着脸。司机突然指着前方,透过纷飞的雪片,隐约可见点点火光——那是破冰船在开道,是运输队在卸货,是守军在点燃Molotov鸡尾酒。当第一颗照明弹升上夜空,我看见冰面上用德军残骸摆成的巨幅标语:“斯大林与我们同在”。
手掌按在胸前的证件,指尖触到里面夹着的麦穗——那是纳罗-福明斯克的农民代表送的,此刻带着体温的种子,终将在列宁格勒的冻土上发芽。我知道,这次行程不是冒险,是钢铁般的誓言:当领袖与人民共同站在冰面上,任何封锁线,都将在“乌拉”的怒吼中崩裂成齑粉。
裂冰穿甲北风号,铁马冰河卷雪涛。
且看赤旗熔弹处,半湖星火半湖刀。
1942年1月3日凌晨三点,吉斯-5卡车的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两道模糊的弧,冰层下的气泡声透过钢板传来,像德军潜艇在窃语。马林科夫的膝盖抵着伪装成货物的电台箱,手指在地图上标出的“冰裂高危区”画了个圈,羊皮手套边缘露出他标志性的蓝宝石袖扣——那是1936年莫斯科党代会的纪念品,此刻却用煤灰抹得发黑。
“前面就是‘狼嘴’弯道。”司机瓦西里转动方向盘,车灯光柱扫过冰面上的弹坑,那里冻着半截德军降落伞,伞绳上的“卐”字被利器割得支离破碎,“三天前第9运输队在这儿被斯图卡炸沉三辆车,现在冰面下还冻着没捞完的面粉袋。”
我摸了摸腰间的PPSh-41,枪托上的“察里津1918”刻痕硌着掌心。马林科夫突然按住我的手腕,耳麦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贝利亚的密电,德军侦察机从芬兰湾起飞,预计七分钟后抵达编队上空。”他掀开大衣,露出别在腰后的鲁格手枪——那是从德军少校尸体上缴获的,枪管刻着模糊的东正教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