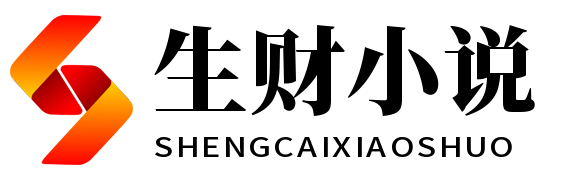小说:穿书白月光:反派,你别哭啊 小说:古代言情-女玄 作者:蓝色的胖子 简介:符誉第一次哭,明漪用给岑上雪的万年玄铁锻了把神兵送给他,神兵甫一出世,跃居兵器榜榜首;第二次哭,成功让明漪断了收徒的念头,他成为她唯一的关门弟子…符誉暗里觉得她好骗,早厌烦了她事事干预,利用完后决定卸磨杀驴。后来不用他动手,明漪和本来该成为她弟子的几个人死在仙魔大战中,符誉持神兵黑煞杀出一条血路,却连她的尸体也找不到。...
事实确如明漪所料,来救他们的人正在路上。
离老虫寨正门五里开外的一处茂密的小树林内,树影幢幢,正午燥热的阳光寻缝隙洒落,降了些许热度。
派去观察地形的捕快小跑着回来报告,“老虫寨把守的哨兵两个时辰一换,换哨的时间很短,估计潜不进去。”
蓟县位于齐州东南角,匪患横行。
老虫寨是蓟县最大的匪寨,独自占了一个山头,里面的山匪狡诈至极,多剿不灭,实乃县衙心头大患,县令府派了好几次兵也没将对方剿灭,反倒被对方耍得团团转。
小捕快急得满头大汗。马军师却对身边的叶涣叶二公子却说起了不相干的事,一双眯眯眼含笑,抬袖指了指老虫寨的寨旗,燥热的风吹过,上面的老虎迎风张牙舞爪,凶相毕露。
“二公子,您说是这老虎厉害呢?还是这打老虎的武松更厉害?”
叶涣一身白衣,身背箭囊,斜挎一把做工精良比县令府的捕快不知好上多少倍的弓,立于山林间也不损他叶二公子的雅度,此时颇为苦恼地拱了拱手,“您莫要打趣知雅了,青青正在寨中为人质,知雅只想快些将夫人救出来,让她少受些苦。”
叶涣没在县衙当差,此次会同县衙一同前来剿匪,为的就是其夫人。
“早闻二公子宠妻无度,今日所见不假。”马军师捋了捋花白的胡须。
叶涣字知雅,是蓟县地头蛇之一叶家的第二子,自幼聪慧,温雅端方,上贤下孝,是蓟县所有未出阁的姑娘的梦中情郎,只这情郎早早成婚,娶了平民邓家的小女儿邓青青,先不说二人成婚那日多少少女心碎了一地,就邓青青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故事就羡煞了多少女子?
更说叶涣成婚两年,邓青青两年无出,他更是顶着家里的压力坚决不红袖添香,连房妾室也无,这样的好男子世间难寻。
叶涣急得想直接冲进去,“我们何时才能动手?”
青青在里面待了三日,现在不知有多害怕。
“莫急。”马军师捻捻胡须,“对方人多,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等天黑。”
确实不是动手的好时机,如果能动手马军师已经率人施救,里面的人都是蓟县有头有脸的人的亲眷,近些天县令府的鼓都被这些人敲烂了,马军师比任何人都想平安地救出他们。
但蓟县县令府的情况,人数倒是说出去骇人,但三个二个老弱病残,再不然就是花拳绣腿三脚猫功夫,和真刀真枪的山匪们直接对上,怕还不够人家切瓜磨刀的。
这时冲来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黑红的捕快服紧紧贴在他紧实的胸肌上,抹了把额上的汗,没有和马军师打招呼,直接问叶涣,“我们什么时候救青青?”
是邓青青的大兄邓大。
叶涣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现在不行,等今晚。”
邓大心大,没觉察到自己被嫌弃了,大叹一声,“还要等天黑?这如何是好?青青要是有个好歹…”
叶涣自然也心急,但此时多说无益,他垂下眸,转身离开,“我去那边看看。”
这…
邓大看着他脸色难看地走了,一时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他了。
“叶夫人水深火热,二公子难受也属然人之常情。”
马军师摇了摇破扇子,开解道。
也是。
马军师的话让邓大倏然解惑,不过他并不因此对马军师有多余的感激,潦草拱了拱手,也匆匆回岗位监视情况去了。
他那钓了金龟婿的妹子还在受苦受难呢,他哪能有心情管别的?
以邓家攀上的这个高枝,邓大确实也无需对县令府一区区军师卑躬屈膝。
原先那名报告的捕快啐了一口:“狐假虎威的龟儿子!”
马军师笑意不减,静等天黑。
寨内。
闵良跨坐大堂上首,左手提了一坛酒,大灌一口,仰天大笑,“这票干过了以后,闵某请兄弟们大吃一顿!” 这票都是肥羊,不怕宰不出油水。
底下高矮胖瘦的山匪们齐齐欢呼,热闹得像过年。
“有肉吃咯!”
“干了!”
有人起哄:“老大不如把你珍藏的酒给兄弟们过过瘾?”
闵良嗤了声,举杯一动,胸口至左臂的老虎图腾也像活了过来,粗犷的声音道:“那些酒算什么?今儿个大伙吃完这一顿,明天真正的庆功宴请你们喝更好的酒。”
今晚吃饱喝足,明天才能更好地干活。
众人又是一阵更大的欢呼。
符誉本来在角落冷冷地注视着土匪们的狂欢,今天看到每天天没亮就出门的三兄弟一睡睡到大中午,他就猜到换人质的日子快到了,只是没想到闵良动作居然这么快。
看来今晚就得离开这里。
这时上首的闵良目光一扫,鹰隼般的眼睛眯了眯,落在他身上,冲他招了招手,“你,过来。”
符誉一惊,忙敛下眉目,再一抬眼讨好地到他身边,“您有什么吩咐?”
闵良健壮的手臂捞过他瘦弱的身体,毫不用力就把人按在了他的专属座椅上,赤裸的上身贴着他的衣服,大嘴中吐出酒气,“你小子这几天表现得不错,今天晚上来我的房间。”
平心而论,符誉除了皮肤晒成了小麦色,就他的立体的五官、天生带几分邪气的眼睛、斜飞入鬓的眉毛来看,长得十分出色,当然,他的肤色也不能称为他的缺点,至少给这毛都没长齐的少年去了几分奶味。
符誉脸白了一瞬,几乎马上望向羊成的方向,却没想到正好对上那张惨白的脸上也正看着他的狐狸眼。
见他看过来,一展折扇,绽出一个自以为风流的笑。
符誉假装没看见,垂下头,乖顺地“嗯”了声。
“去吧。”闵良拍拍他的肩。
符誉僵直地走回自己的角落,他知道闵良在看他,故意装出羞涩的不知所措,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脑海中却闪过无数种杀人的办法。
老虫寨的土匪全都这么恶心?有女人不睡,都想来睡他?
符誉不得不这么想,刚刚和他对视的羊成,这个土匪寨子的二当家就曾表露出想睡他的想法,只是这两天他每天早出晚归给他们打猎做饭,每到深夜累得倒头就睡,没给羊成真正占便宜的机会。
听睡床上的土匪们说,羊成晚上来找过他几次,但他睡得太死了。
身边靠近一股浓烈刺鼻的脂粉味,羊成还不嫌那臭味大,卖弄风骚地扇了扇团扇,在他胸口点了点,惨白的脸带着红艳的唇放大在他眼前,“小家伙还挺受欢迎。”
大哥男女不忌,羊成是知道的,他也曾经想过上闵良的床,毕竟那一身肌肉看起来就很好摸,但他脱光了躺他床上他也看不上他。
虽然小家伙得到大哥的青睐这一点让没吃到闵良这块猪肉的羊成略微不快,但看到符誉那张不痛快的俊脸,这点儿不快又变成了想跟大哥喝口肉汤的快感。
这样的人在那方面反抗起来肯定更带感。
毕竟这小家伙,他可馋了三天呢。
符誉笑出一口白牙,丝毫看不出怒,“比不上您。”
王三放水时没管住嘴,说羊成把老虫寨的人睡了个遍,王三本人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还说和他睡绝对是遭了大罪,说起这件事时嘴唇苍白,显然是想到了不好的回忆。
羊成一噎。
这话和说这话的人的表情都像在夸他,但羊成总觉得笑得天真无邪的这小子并没怀什么好心,就像他说的话也不是什么好话一样。
“外面是什么声音?” 赶上晚饭,垫了垫肚子,明漪的五感才明显了些,不过也可能是外面的喧哗声更大了的缘故。
邓青青想说每天都这样,但仔细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在上方踩踏,地牢里听外界的声音都要仔细辨别,今天声音果然比平常都大,脸色白了白,“他们不会要宰了我们吃肉吧?”
在暗无天日的牢里待了三天,有什么最坏的念头都不奇怪。
这句话在地牢里激起不小波澜,小孩们吓得哇哇大哭,“娘亲,我不想被吃。”
“别怕别怕。”大人把小孩搂进怀里,拍着拍着他们的后背,自己不由也带了几分颤音,“娘亲会保护你。”
人心惶惶,生死面前,没有人会不害怕。
但明漪觉得不可能,他们被关了三天,一个人都没有少,哦不对,少了据说是这姑娘的奴隶——如果不是半个时辰内邓青青咒骂了那个奴隶十次以上,明漪也不会知道这一点。
可如果真是绑了他们为了吃肉,为什么不在他们最肥的时候吃? 还有怎么会这么巧,这里除了她,其他人看起来都很有钱。
“别自己吓自己。” 不过她现在的处境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这句苍白的话没再能安慰到邓青青,也没能安抚相拥痛苦的大人小孩。
他们都沉浸在可怕的幻想里,这么久都没人来救他们,真的要等死了吧?真的要被活活煮成肉骨头了吧?
这世道并不太平,坊间早有传闻有些县的农民饿到昏厥,联合起来将地主剐了吃肉的例子,那时不当一回事,此刻无限放大,成为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邓青青又抱着膝盖呜呜的哭起来,靠明漪紧了些,“大师,救兵什么时候到?”
明漪也不知道,但她的手再碰到邓青青的手时,心内一沉,救兵再不来,恐怕要等不及了。
夜凉如水,牢里哭累了的小孩依偎在娘亲的怀里,带着白天的恐惧入睡,眼角还有泪痕,明明没有一点力气,还要紧紧抓住娘亲的衣袖。
他们和身边的邓青青一样,对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对土匪、对未知充满了害怕。 明漪轻轻叹了口气,在心里说,对不住了。
晚上,东屋的烛火通明。
符誉紧紧捏着手里的药粉,掌心冒了汗,将包药粉的叶子打湿,绕过几个梁柱,朝闵良的屋子走去。
叶子里包的是他在山上采的三毒草、红蘑菇杵成的汁水晒干后的粉,他的匕首被没收了,这是他唯一想到的能撂倒那个彪形大汉的方法。
少年站在东屋门前,印在纸窗上的影子正在擦拭一把匕首,他目光阴沉地盯着那个影子,深吐了几口气,推开门,挂上假笑。
谁知,刚一进门,冰冷的匕首贴上了他的脖颈。
“啪嗒。” ,药粉掉到了地上。
符誉呼吸一滞。
没有药粉,他对上闵良的胜算为零。
这是一个比山中猛兽更健壮的男人,当他对他有戒备时,更是如此。
闵良只看了一眼地上散落的白色药粉,锋利的刀面没入了一线,阴沉沉地笑,“果然不安好心。”
符誉仰着脖子,脸色煞白,死死盯着比他高一个头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自觉在今晚以前从来没表露出过杀心。
“嗤。”闵良换手掐住他的脖子,刀面在他好看的脸上拍了拍,“这点伎俩也看不破,你当老子怎么当上寨主的?”
闵良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他不是能被驯服的狗,不过十几岁就知道卧薪尝胆,这样的人,只会在背后狠狠撕下你一块血肉。
闵良不期望能驯服他,也绝对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心头大患。
正要动手,外面传来惊慌的大叫,同时纷杂的脚步声涌向四面八方,“不好了!官府来了!”
“快逃!官兵来了!” 火把来回闪动,闵良操了声,“格老子的!”
随即一刀捅进符誉胸腔,狠狠拔出来,把他摔到地上,匆匆去看情况了。
这一刀本来应该捅在他正心口,但符誉很快闪避了一下,闵良被动静吸引,没来得及再给他补一刀。
符誉吐出一大口血,用尽最后的力气仰躺在黄土地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却让他的意识更模糊。
耳边惨叫声缭乱,纷杂的脚步响如震天,整个院子都乱了。
但那些声音都逐渐远去,符誉望着天上微弱的星光,忽然想起了一些很久远的事情。
每次、每一次他到了要死的关头,总会奇迹般地活下来。
最早的记忆是在羊群里,和一群臭烘烘的羊一起,靠着它们的奶活下来,后来是在邓家当牛做马,一个冬天脚底打滑,摔断了一条腿,邓家人没发现,是他自己爬回去,自己去找猎户讨药活下去的。
再后来是冠上奴籍,他握着柴刀,发疯一样去找他们拼命,最后挨了三十大板,皮开肉绽,靠求叶涣活了一命。
符誉本来应该对再一次直面而来的死亡感到恐惧或者愤怒命运对他这么不公,但现在他脑子里的全部想法是:下一次管什么尊严呢?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