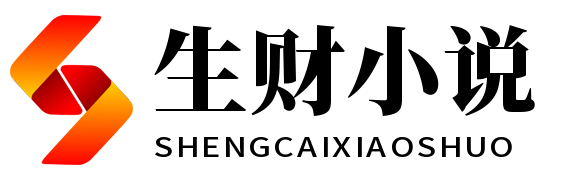小说:战国大混混 小说:历史 作者:阿拉贼胖 简介:青年穿越到战国末年,发现自己的新身份是个混混!也罢,既然当混混,就要当战国最大的混混。数数战国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不管这天下姓嬴还是姓刘,想来我这一亩三分地搞事情,都要给我三分薄面!(轻松不小白,作者尽量考证,还原一个真实的战国世界……) 角色:崔致,赵人耳 《战国大混混》第1章夤夜搏杀免费阅读 皓月当空,轻云遮月。在通往贝丘县的传道上,一辆...
黎明前的黑暗里,万籁俱寂。
一只鸡卧在鸡埘的横木上,闭目而眠。
东方的天际微微透出一丝光亮,露一点鱼肚白。
只过了一会儿,光比之前更亮了些,光线照到歪斜下垂的鸡冠上,映得鸡冠如血。
鸡的眼睑(jiǎn)突然睁开,一阵张急促的抖擞甩掉身上的露水,昂起头“咯~咯~咯”鸣叫起来。
这是一个羽毛上有青色花纹的矫健公鸡,承担着曲防里每天报晓的任务。
随着它的一声高鸣,曲防里其他家里的鸡也被吵醒,由东向西一阵接一阵蔓延开来。
曲防里新的一天也就开始了。
青豚在妻的催促下骂骂咧咧起床了:“戊什王叟家的那只青花鸡,每日天不亮就叫,乃公迟早盗了杀来吃!”
妻笑骂道:“哪里天不亮了,你去看,都亮半边天了!”
“我们里的鸡鸣,比隔壁里要早一个刻的时间!每日平白多做一刻的工!”
青豚简单洗洗脸,拿右手中指在牙齿胡乱擦了几下,用水漱了口,夫妻俩带上一斗半的粟米,出了门一齐向张家走去。
青豚夫妻二人无子女,在张家复除。
复除就是免除徭役,张家家主张寇,通过考核成为了武骑士,也就是赵国的骑兵,从平民一跃益爵五级,待遇堪比贵族,自此全家可免除徭役。
因此慢慢就有想逃避徭役的人依附到张家,把自家的地挂到张家名下,自己名义上是张家的人,借此可以免除徭役,跟后世帝都假结婚汽车号牌过户一个道理。
所以想要复除,你家必须有地。
青豚的父亲,活到三十七岁就死了,死在一次徭役中。那是一次冬日的采冰,青豚的父亲不小心掉入冰窟窿中,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成冰棍了。
他父亲从十七岁附籍开始,每年要为县府无偿徭役一次,一次个月;贝丘县的徭役无非就是修河堤、修筑城、运粮、凿冰运冰此类,父亲全都做过。
按规定,每人一年一次徭役,但父亲二十年的徭役生涯中,却服了30余次,到了战时,征发徭役往往没有规律,有时候一年两次征发都是常事。
好在青豚的父亲是曲防里第一代移民,自己拿着石头做的农具,硬是在河床上开了八十亩田;种到第二年,来了几个乡县的吏,他们丈量了土地进行登记造册,青豚家的田就被划分成了“行田”。
跟因功得爵授田的“功田”不同,行田所有权是国家的,人老或死,国家收回,再分给其他人。但实际执行中一般都是父死子继,于是青豚的父亲死后,户主就变成了青豚。
青豚再也不想像父亲那样去做辛苦的徭役,与妻一合计,干脆去张家复除算了!
可张家也不是什么地都要收的。
低于五十亩不收,获利太小又有法律风险;薄田不收,投入高产量低,获利也不高。
好在青豚家这八十亩地算是中上田,不用肥田,拿来就有产出,张家痛快地接受了。双方私下定了契约,青豚就正式在张家做了复除,名义上,他成了张家的隶臣、家奴;但实际上双方各取所需,一般来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做了复除以后,除了要给官府交的十一税,还要给张家再交两倍。十之三交出去只留其七,听起来挺亏,但青豚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甚至比做自耕农时还要好些。
其一,每年一月的徭役免除了,青豚可以多些时间在地劳作,也可以做些副业,改善生活;
其二,张家的牛马铁具,比自家好多了,有了牛、车、铁农具,农活的强度低了,青豚也有更多时间去做他事;
其三,张寇作为里典也富有贤名,时常接济困厄,遇到喜事节日偶尔也会分些酒肉。
因此做了复除的青豚反而成了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家中鸡猪狗齐全,不必顿顿粝(lì)米下饭。
也正是如此,青豚与那些自耕农、半自耕农不同,他可不必每天着急赶着力田劳作,以至于每天听到鸡鸣都会为那“多出来的一刻”气愤不已。
青豚夫妇背着一橐粟米,提着陶釜,到了张家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四五户人,有复除,也有佣耕。
众人寒暄了一会儿,张家那青石门楼的大门嘎吱一声缓缓打开了,众人拾阶而入,去一进院领取农具车牛。
青豚进去时,少家主穆生正蹲在地上,左手持竹杯,右手中指沾了一点青盐,动作舒缓地细细擦洗牙齿。
“啧啧,什么时候乃公也能用盐盥漱啊?”青豚一阵羡慕。
其实张家虽是大户,但平时也是舍不得不用盐盥漱的。这时候哪怕是青盐也要一百多钱一斗,张家上下十几口人每天用盐擦牙,一年下来也是笔庞大的开支。也就穆生这个读书人娇贵罢了。
待到青豚牵了马,给马套上了辔(pèi )头,穆生突然道:“青豚大兄!”
“穆生唤我何事?”
穆生走过来说:“听闻你与我堂兄张急少时是玩伴,可知他亡走之后去了哪里?”
青豚张急忙否认道:“我与那恶人张急只是偶尔玩伴,我家在东,他家在西,平时也甚少走动,是以不知他去过哪里。”
穆生想想也是,既然亡走,怕是不会透露自己所在的。于是别了青豚,自己在堂中踱步。
一边转着圈,一边脑中思考:这黄石公是否确有其人呢?
其实昨晚王叟来访,将自己与张急的约束告知后,穆生一开始是拒绝的。
方今天下显学唯有儒墨法,但所谓学问,又岂是儒墨法三家能涵而盖之?仅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有道、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各有拥趸(dǔn),出师有名而开枝散叶者又不知几何?!
再者说,楚国极盛之时地方五千里,如今也有两千余里,人七百万,其中能人异士者不知几何?哪怕东方的吴越、南方的洞庭等披发左衽、断发纹身的蛮夷之地,也有计然、陶朱公那样的国之大才啊!
张急要是非说在楚国哪个旮旯有个叫黄石公的隐士,谁去大老远求证去?
可如果我不知道,乡里之民岂不是要说我连个“恶人”都不如?
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暗骂起始作俑者来,呜呼!你们之间的约束和嫌隙,为何拉我下水?
正在穆生踌躇纠结间,屋内却传来一声大笑,随之一个头戴进贤冠,留着一副美髯的中年人走出来,道:“穆生未有盛名岂有盛名之累乎?”
那人摇头又道:“传道解惑是一种名望,礼贤下士也是一种名望,不耻下问也是一种名望啊!”
穆生闻言怔在堂中,随后说:“申公所言有理,穆生谨受教!”
而后又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双手缓缓高举齐额,俯身推手,郑重行了一个天揖。
申公却视而不见,犹自晃着脑袋说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那个叫张急的从兄,过去虽然任气为害,但‘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申公言罢又突然冷冷一笑,道:“午间的见证,我与你同去。”
穆生问:“申公送我回乡,本来今日不是要出发去邯郸游历吗?”
申公淡淡地说:“能作出‘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的诗句,说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话的人,他所学的《致富经》是何学问?我倒是想一探究竟!”
其实申公未明说的是,这个时代只有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才能称之为“经”。
在申公这样的儒者看来,一切非儒的学问都不能叫《经》!君不见墨家作了本《墨经》,儒墨两家几百年来不死不休,直到墨家一分为三,实力大减才偃旗息鼓。
虽然此时也不乏有范蠡作《养鱼经》之类的“杂学”,但都非显学。那些不入流的学问,就算冠之以经,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是假如有人心术不正,以“经”的名义去欺诈世人,愚弄生民,那作为立志于修齐治平的申公来说,少不得要除魔卫道,将这淫徒恶少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是作为一名鲁儒的使命!
所以这个“热闹”,申公是一定要去凑一凑的。个中缘由,却不必道之于穆生了。
申公说完又哈哈大笑,抓着穆生的手要回屋早读。
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鸡鸣就要起床,起床就要读书,一刻也不能浪费。
“我怎么觉得里中的鸡鸣要比曲阜早一些呢?”
带着疑惑,穆生随申公走进了屋内,随之传出“子曰”“之乎者也”的读书声。
青豚和妻牵牛下了田。
谷场看谷的人家也纷纷醒来,回家取了粟米拿了农具,再去田中刈粟收割。
王叟一家也出了门,带着铚,还有那把崩了口的䥽镰向地里走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干的事,除了张急。
昨晚月帮他找到了那样关键的东西,他忙活了一夜,做了几遍,终于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出来了,如今正在静静躺在釜中。
家中也被折腾的乱七八糟,里外到处瓶瓶罐罐且充满了柴火味,睡也睡不着,干脆不睡了。
他此刻正躺在门外的一处禾杆堆里,嘴里叼着半截秸秆,对着两个小朋友讲故事。
只听他声情并茂地讲道:“……话说在那极西之域有一处极高的山脉,名为昆仑山,山中产玉,为昆仑宝玉……”
一个髫童吸溜了一口鼻涕,说:“恶人急讲的不好听,西王母的故事我都听了好多遍了!都是套路!套路!”
张急低吼一声,冲这髫童作发怒状,唬道:“谁说这是西王母的故事了?好戏还没开始呢,这是铺垫啊懂不懂?一共就几章铺垫,又不要你钱,必须听!不听我就吃了你!”
髫童小嘴一歪,眼眶中瞬间一股热泪打转,憋着不敢哭出声。
张急继续讲:“……山上有一灵石,上书五个大字‘泰山石敢当!’”
另一髫童插嘴道:“为何昆仑山上的石头要刻‘泰山’两个字啊?”
……
“我赵人信奉的霍泰山之神,乃是西王母之子……好了不要问与故事无关的问题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累不累啊,好听就对了……来,张急叔叔接着给你讲啊……话说那灵石吸收了日月之精华,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突然崩开,生出一石猴……你看,好听的这就来了……”